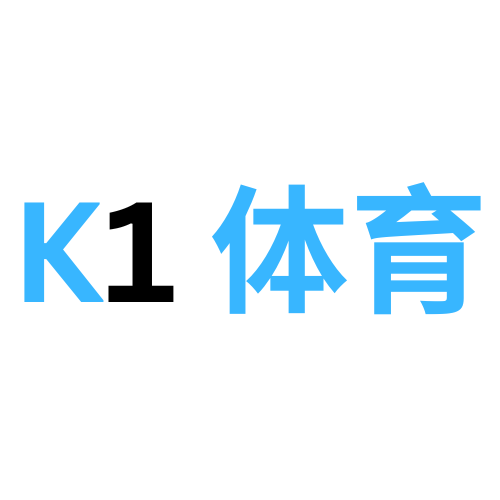新闻中心 News 分类>>
1k1体育有自行车的地方就有“偷车贼” 世界自行车日
k1体育今天,是第3个世界自行车日。2018年4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致决议,将6月3日设定为世界自行车日,鼓励会员国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推广自行车的使用。
作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目前中国的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近4亿辆,位居世界第一。无论是现在上下班高峰期川流不息的各色共享单车,还是五十年前与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并称“三转一响”的结婚必备品,自行车一直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典籍中关于“自行车”的记载早在明朝末年就已出现,热衷于发明创造的陕西青年王徽(1571-1644)在他的《新制诸器图说》中绘制了“自行车”的雏形。不过中国人真正骑上自行车,还要等到十九世纪末,来华传教士把英国式前、后轮小的自行车带到中国。
当时最为著名的骑车人要数末代皇帝溥仪。他不单在紫禁城开辟了一个专门的运动场用来骑车、打网球,为了骑行方便,还让人锯掉了故宫二十余处门槛,储秀宫东侧门的门槛锯口至今犹在。

一百多年过去,自行车的名称从“洋马”、“洋驴”、“风火轮”、“自有车”固定为今天统一称呼的“自行车”,骑车人也从达官显贵、豪门巨贾成为寻常百姓,自行车的款式、性能更是更新了好几轮,唯一不变的只有“偷车贼”这个职业的存在。
根据2007年大学的一项统计,全校3万名学生中有近2万人拥有自行车,在持有率高达七成的同时,自行车失窃率也居高不下,平均每人在大学四年间都要丢一到两次自行车。“丢失一辆自行车”或许能成为所有学生毕业时的共同回忆。
即便在治安良好、经济发达的瑞士,自行车盗窃案也是局的一大难题。据统计,2010年瑞士有4万余辆自行车登记失窃,破案率仅1.6%,根据警方估计,未登记的失窃自行车每年至少有10万辆。

共享单车普及之后,偷窃案件也随之水涨船高。今年五月,沈阳市就破获了一起“特大”共享单车盗窃案,民警在某小区库房里发现了8辆车锁被严重破坏的共享单车,对破坏车锁、非法占有单车的人员处以10天行政拘留。
遗憾的是,从自行车发明以来,人们绞尽脑汁也没有找到办法解决车辆方便搬运、不易保管的技术缺陷,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至于“偷车贼”这一职业始终与自行车相伴相生。
晚清中国的报纸中,时常可见“窃脚踏车”、“又窃自由车”之类的新闻报道。直接理由当然是偷车一事有利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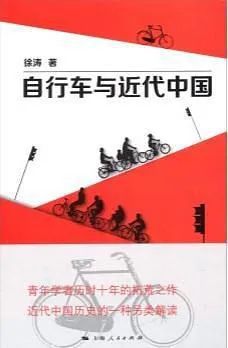
据历史学者徐涛在其《自行车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分析,自行车刚传入中国时皆为进口,价格不菲,倒卖车辆利润颇高。20世纪初,一辆普通自行车的价格在80元上下,相当于今天一辆中档汽车的价格,高端品牌的自行车则价值更高。赃车一旦得手,便脱手换现,虽然倒卖价格受行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大致也在40元左右。而当时普通雇员的月工资不过十几元,一辆赃车的收入少说也抵得上两个月的工资。
在巨大利益下,近代中国城市出现了一批“专事偷窃脚踏车为生”者,其中甚至有部分不受境内法律约束的外国人。1909年10月22日的《申报》就以《惯窃脚车》为题,讲述了一位名叫“非立司”的洋人以偷车为生、被捕快抓获的故事。
徐涛认为,中国近代的自行车偷盗问题难以解决,有其深层社会原因:一是近代以来,中国各大城市都开启了现代化转型的进程,城市不断吸附新移民,人口规模日趋膨大,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所谓“游手好闲”之人亦日见增多,偷盗问题也日趋严重。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之后,一项调查表明,“从事不正当职业”即专事偷盗或行乞的人,约有2万人。二是自晚清至,偷盗虽为入刑之罪,但对于普通的偷车行为,法律无法重罚,更没有有效手段阻止再犯。偷车贼因而往往成为惯犯,偷车也因此成为常业。
现代化转型中城市人员增多,针对偷车没有合适的惩罚防范措施,这两点理由似乎同样可以部分解释今日自行车失窃案频发的原因。可见历史总有着相似的逻辑。
若是只有偷车贼顶风作案,赃车的倒手变现并不会那么容易,一次两次可为,三次四次到哪儿去找那么多“二手车买家”呢?
当时自行车价格昂贵,骑车又是不可不赶的时髦,自行车出租业务应运而生。但考虑到租车人的支付能力往往有限,租车行的定价亦不可太高,为了盈利,只能在店铺车辆上做手脚。
修车铺也是同理。如徐涛所说,在整个华商自行车营生行当中,修理、出租自行车业因其技术、资金、人员门槛较低,因此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在整个自行车行业的产业链条中处于边缘位置。从业人员往往会选择非常规手段,游荡在法律规范的边缘地带。
偷车贼偷来赃车,或卖给租车行以供出租,或卖给旧货市场以供出售,再不济也能将零部件交给修车铺。而出租、出售的二手车难免又到了偷车贼手中,如此循环往复,自然利润无穷。

《自行车的回归: 1817—2050》,[法]弗雷德里克· 赫兰著,乔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当时的车价不比今天,丢失一辆自行车相当于半年的工资打水漂,为了防贼防盗,爱车人也花尽了心思。作家吴祖光曾回忆自己拥有第一辆自行车时的心情:“天黑了我把车推到卧室里,端详,抚摸……夜里睡不稳,一夕数惊;几次开了电灯,起床看车子在不在;车子是好好摆着的,有黑有白,发光发亮;但我终于搬了一张小凳子坐下看着车子,直到天明。”可见对于自行车的宝贝之情。
于是另一方面,自行车失窃的问题直接促成了另一个新产业的诞生——自行车寄存处。此类自行车寄存处,相当于现今的收费停车场,为自行车提供停放和保管服务,按时收费,另需押金。寄存处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沈阳的北陵公园,很快便在全国各地打开市场。尤其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由于多数公共场所不许自行车进入,自行车寄存处便满足了爱车人的需要。虽然寄存自行车一小时的价格(五分)抵得上租赁自行车(一角)的一半,保管还不对车辆附带品如车灯、车铃等负责,但相较于失去爱车的痛苦,实在是微不足道。
最初的寄存处均为私人营业,直到1946年上海市政府统一收编了沪上自行车停放站的经营权限并加以整顿,外包给指定公司经营,是为“沪通脚踏车停放站”。“沪通脚踏车停放站”在上海设立了上百个,囊括舞厅、剧院、公园等几乎所有公共场所。
在徐涛看来,公权力进入对自行车的管理,乃一举多得之事:一是可以整顿市容;二是能够减少自行车失窃,保障市民权利;三则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缓解失业问题;四来收取的停车费用也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另一方面,由偷车贼衍生的销赃产业链和自行车寄存处的此消彼长也可看出,自行车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普及性工业品,绝不仅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交通方式,更是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生产业态乃至创造了新的经济环境,并对政府的城市治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6年共享单车的大规模出现,向各个城市的交通管理部门发出了灵魂拷问:如何避免自行车偷盗事件的发生?是否有足够的城市空间供自行车行驶和停放?大量自行车上路后之后,如何规范行车、保障行人安全?
1923年8月,《申报》刊载专文讨论如何应对自行车盗窃,并提出了三条“补救之法”:一、最好于英法租界当局,给予照会,编成号码;二、自己之脚踏车,购时费价几何,亦须存藏,最妙莫如于车之隐处,刻极细之记号,俟觅得偷者时,即指此为证;三、脚踏车既被盗窃,切不可声张,宜于失窃后第二日,着手寻觅。
三项建议中,最为可行也最具前瞻性的无疑是第一条:由市政当局发放牌照,悬于车身,以供随时检查,正如现在的机动车管理办法。
为自行车发放牌照的方式最先于20世纪在上海租界实行,随后20年间被中国其他城市普遍接受、使用。按照法律规定,任何来源的自行车在上路之前都要由车主凭借购车前往相关市政部门登记,并领取对应且唯一的号牌与执照(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机动车牌照和机动车驾照),缴费后将号牌悬挂于车辆明显位置,行车执照随身携带,以便查验。如此一来,如若自行车失窃,则可根据号牌按图索骥追回。
针对偷车贼销赃的黑色产业链,上海特别市公用局在1944年“特布告各脚踏车行,遇有出售脚踏车者,应查明来源及证件证明,方可接受”,北京特别市政府局也发布了《规定取缔收售修理旧脚踏车暂行办法十五条》。

正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此严防死守,偷车贼仍有空子可钻。为了规避自行车号牌、钢印等车辆标识所带来的被捕风险,偷车贼在偷获车辆之后立刻用锉刀将车上的钢印锉去,再把自行车大卸八块拆分成各个零部件送往旧货商处出手。旧货商则再三转手,将零部件运往号牌并不通行的其他城市,重新组装成车辆之后再出售。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每个局分局每天至少都会收到十余起丢车报告,盗窃之风不止。
可见自行车牌照并不能从根源解决失窃问题,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实践已经向我们证实了这个事实。尽管随着科技发展,各式车锁的安全性能不断加强,不少自行车也装上了GPS定位系统,但另一方面,偷车贼的技术水平也与时俱进,而自行车本身的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为自行车安装防盗设备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防盗的性价比。

既然偷车是为了赚钱,那么随着自行车持续贬值,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是不是自行车失窃率就会下降呢?
倒也未必。一来相较于偷车几乎为零的成本——偷车技术简单、案件破获率低、即使破案惩罚也算轻微,偷来的自行车虽然远不如一百年前值钱,也算一笔不亏的买卖;二来对于贪小便宜破坏共享单车车锁的这一部分偷车贼而言,他们图的只是随手使用自行车的便利,并不在意自行车的市场价格。
今年五月,杭州市一派出所破获了一起自行车偷盗案件。涉案的自行车售价近一千元,确实价格不菲,但对它暗生贼心的却是一名月入过万、从事医药工作的博士。而监控中的他,明显是有备而来,拿出一把钢锯干脆地锯掉了车锁,转身就骑走了车。所以自行车失窃率似乎和自行车价格或者经济水平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自行车的地方,就有偷车贼。从自行车出现伊始,骑车人已经和偷车贼斗争了一百多年,但这个问题至今无解,只能在爱车尚在的时候,且行且珍惜。

 2024-10-20 15:20:15
2024-10-20 15:20:15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